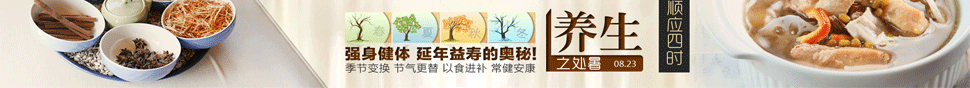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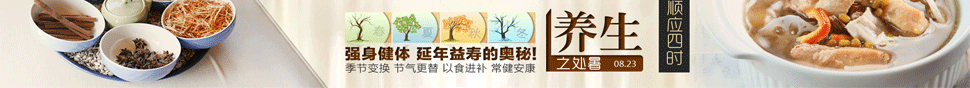
作者杜正贞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年第4期,注释从略
专题论文
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的获得与证明
——浙江龙泉县与建德县的比较研究
杜正贞
一、山林所有权的法律变迁
林业史对中国历史上山林的所有权,常常只是笼统地定性为“官有林和私有林”“朝廷和各级官府占有”“私人占有”或“地主阶级所有制”“农民阶级所有制”等。这些抽象的概念,并不能让我们了解古代山林所有权的观念和实际占有的状况,也忽视了这些问题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区域差异。唐长孺梳理了山林川泽从国有(天子所有)到被迫承认私人占有的过程,他指出:“山林川泽在古代一向不承认私人有占领的权利……在中国似乎维持山泽公有更久,直到出现了国家以后,便算作天子所有,私家还不能占领……随着皇权的消长与禁令的宽严,对于山泽的控制虽不能常常十分严格,但山泽王有的法律依据却始终保存。”根据他的研究,南朝刘宋时期,羊希立法承认私人(主要是豪强、品官)对山泽的占有。这是在山泽开发的过程中,国家试图对豪强大族以及山泽之利进行管辖的一种努力。但是,唐长孺也证明了这些限制和管理都是不成功的。
唐宋以后封禁或弛禁山泽的政令,所针对的主要是皇陵、园囿、名山等一些特殊的山林,它们被认为是“国有”或皇家专有,设专门的官员管理。但对于其他广大的山林地,国家并没有常态化的管理机制。与田土很早就因为赋税而进行了清丈,并建立起砧基簿、鱼鳞册等官方档案相比,除了徽州等地之外,山林的赋税记录相对较少。在漫长的帝制时期,有大量的森林都处于法理上“国有”(天子所有)和事实上“失管”的状态。
在上述制度背景下,明清时期民间山林开发过程中,自发以契约的方式形成林业的产权市场和经营秩序,即林产的占有、转移和买卖都仅依靠契约为凭据。这在清水江等林区的研究中,已经一再被证明和强调。依靠近20年来在该地发现的大批清代林业契约,张应强、梁聪、罗洪洋等学者,对这一地区的林业开发、经营习惯和规则,以及社会组织、文化形态等都进行了详细考察。梁聪和罗洪洋的研究主要是从法律的角度进行。梁聪对文斗苗寨契约的分析,特别利用了“法秩序”的概念,分析林业契约在一个苗寨社会中的作用,也探讨了契约所代表的“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
如果以现代国家的标准来看,明清政府和法律对于山林的干预和“权利”保护都是非常薄弱的。《大清律例》中涉及平民的山产林木的法律,仅有“盗卖田宅”条下对盗卖坟山、告争坟山的规定,以及“弃毁器物稼穑”条下对“毁伐林木”的量刑等。特别是《大清律例》乾隆三十二年()的“凡民人告争坟山”例,虽然只针对坟山,但在很多山林诉讼的理断中都被援引。也有很多山林纠纷为了能与法律相合,当事人会以是否在山上有自己祖先的坟茔作为重要依据,甚至多有毁坏、涂改墓碑的控诉。薛允升特别说明:“此等案件南省最多,与北省情形大不相同。”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光绪三十年八月十八日金林养等为控吴礼顺势欺占砍越界混争事呈状”中就有“界内又有身家坟茔赤凿”的申述。又如,“光绪三十二年洪大猷与沈陈养互争山业案”,两造供词中均强调山产内有自家坟茔。据洪大猷供:“监生坟茔有几十穴。”据沈陈养供:“山里他无坟茔,就是小的墓多。”不论法律是否承认、不论是否有契约对山界进行过描述,在纠纷诉讼中,坟茔总是会作为证据而被强调。这种“籍坟占山”的观念和行为在乡民中普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告争坟山”例在承认近年山林的买卖转移以印契为凭的同时,否定了远年契约的证据效力,而是诉诸官方档案,即“山地字号、亩数及库贮鳞册、并完粮印串”。换言之,山林只有开发为山地纳粮升科之后,才能获得官方的认定和保障。晚清新政,清廷设立农工商局,并屡屡颁布各种诏令,振兴林业作为一种求治之道进入各级官员的视野。山林地的开荒植种和所有权确认,也开始成为一些地方官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yinxingyea.com/fbqy/9060.html


